中年人,这里有多少,可以一叙吗? 点击:11049 | 回复:340
常在这里看到中年人发表的看法不一般,但没有年轻人活跃。
中年以上的人,能来这里一叙吗?话题可以广泛一些。比如,工作、生活、对国企的感受;或者,方便的话,可报个年龄。
也欢迎其他年龄段的朋友,说说看法。
20070506补记:
在下面的交流中,我的文字造成了一些理解上的差异。我想,其原因,在于观察问题的角度不一样:
我看问题时,很少关注自身;即使是谈自己经历过的事例,也是放在社会大框架下,把它作为社会现象的具体例子。而且,一些看法或结论,很少是我个人生活的总结,而是对他人言语或体会的一种描述。
20070804又及:
花生网友的“你是哪只毛毛虫?”被顶了出来,我又看到了我的回复,那是我过去生活的写照。今特转来,供参考:
hdss: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-8-31 13:22:00
第5只。
妄想让那棵苹果树长得更好,幼虫时爬过了一段平坦的路;到了可以用自己的眼睛观看那棵树的时候,便按照书本知识试着寻找可施肥之点,不小心挨到一片树叶上,又并未意识到地上的那片树叶,是几位老虫的法宝:只见嗡地一声,天也暗了,地也转了,树叶翻到了我身上。
有声音说:他想吃树根……他在撼树……他以为苹果都是他的……他不信太阳是圆的……他在吃这树叶……
我为了证明:我不是想吃树根、我没有能力撼树、我不是为了得到苹果、我赞同太阳是圆的、我没有想吃这树叶……,于是,我躺在那片树叶下几近一动不动,小心翼翼地不再碰到那片树叶,也不从那下面爬出去;总盼着有一天,会认为,我确实没说假话,是言行一致的。
一直以来,几乎没有谁知道,那树叶下,还有条虫,一直在努力证明着自己;而附近的虫,都知道我是条懒虫、胆小的虫、没有生存能力的虫。
我早就知道,那些老虫们都忙自己的利益去了,也没有谁观察我的言行……他们又有了新的树叶,那片树叶已早被他们忘记了,我无法再证明自己;
现在,在无趣和永久的遗憾中,我探了探头,周围的虫们都忙自己的去了;但我,已无法改变自己,我还在希望那棵树长得更好;在变成蝴蝶前,还会极力地、一点一点、迟钝地爬行着,嘴里、还会含混不清地嘟嚷着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20071121 12:00续记,第6页上,对这帖子的说明(2007-11-20 7:25:00):
本贴的主线是:道德先行、顽强不屈。
一个人向前行走,一路磕磕碰碰,他人看到的似乎只有失败;但他一直向前行,直到最后一份力——从而,那不叫失败,而叫顽强。
(特说明一下本帖的背景:当时有许多的年轻网友,抱怨社会对自己的不公,本帖是想说明,现实是没有天堂的。20081222)
多谢楼上美言!
20世纪70年代觉得60年代是很遥远的过去,21世纪觉得20世纪就在昨天。如果有闲心,无意间经过的历次运动等,也还零星记得:
文革开始那年,我已三岁,所以至今脑海中仍留存有刘少奇画像与毛泽东画像并列贴放的情形——印象中,毛主席着灰色上衣,刘少奇则是黑色的——我不喜欢黑色。接着是“打倒刘少奇”的歌、舞、漫画(以及后来走资派的头像漫画),“打倒刘少奇,他完全搞复辟……”这首歌,现在还可以哼出来。(至1990年代初,参观刘少奇故居时,看到“历史是人民写的”这几个字,又颇为感概)那个时候,我问大人:不加入某个派行吗?回答是:不行!为此我担心了很久:要是加入错了,怎么办呢?(另一个比较担心的,则是毛主席像章的问题,有机会再谈)
林副主席也不是个好人,穿着绿色军装、举着《毛主席语录》永远比毛主席慢半步而紧跟的人,竟然也变坏了。课堂上,因不发给我教材、而且不喜欢我、而使我不喜欢她的女老师,黯然、惋惜、严肃地告诉我们:昨天晚上,林贼偷了架飞机逃跑,摔死了……听得我们鸦雀无声、胆战心惊。以后,就是把以前熟悉、现在惟恐躲之不及的、《毛主席语录》上的林彪图像撕去,再在文章或语录中、找到“林彪”二字划去。
到批林批孔时,已经有相当的觉悟了:不但知道了学龄前看的《四书》是坏书,还对父母亲用封资修的东西毒害我颇为不满——谁要我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呢?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,当然要听毛主席的话、听党的话了。
我用自己的钱,买的第一本书是《孔老二》,第二本是《儒法斗争故事》,还有一本《三字经批注》。在阅读《儒法斗争故事》时,我把“韩信将兵、多多益善”,看成了“多多‘盆’善”——因为那‘益’字的上面两点,象什么羊的角一样,向下弯了弯——直到多少年以后的有一天自我发觉了,才面红耳赤地偷偷改了。
后来据说,那时侯是四人帮横行的时候,大家都说那是一个不好的年代。但我却暗暗感激:割资本主义尾巴时,不准搞副业,使我能理直气壮地顶撞父母(党的话都不听了么),而有了外去玩耍的时间。还有一个特振奋人心的消息,是“八零年实现农业机械化”。
1970年代,在生产队从事过农业生产、种过水稻的都知道,没有星期天、没有节假日的集体工并不好做。夏天双抢时,凌晨4点甚至两点就要起床,早餐后直到中午12点多才能收工:那时分,烈日下,烫水里,腰弯下了就不能直起来,否则汗水会流到眼睛里而睁不开;又不得有半点闲工夫,否则跟不上趟——那,对我们6~7岁、10来岁的小孩来说,拼的,真正的是毅力——我一直很感谢有那段生活,否则在我后来的时间里,早就已经跨掉。熬了几年,到1976年8月,我终于获得了“双抢标兵”称号,虽然奖状上错了两个字(也仅仅只错了两个,很感谢“姓”写对了,“名”的字数也对)。
<img alt="" src="http://ftp.gongkong.com/UploadPic/temp/2008-
学生时代的许多奖状奖品基本上都不见了,惟独这张奖状,由于我当时很珍爱、不同意贴到墙上,而终于保存了下来,幸运之至,幸运之至。基于上面的原因,对“八零年实现农业机械化”憧之憬之。
有时候,由于没有种植规定品种的低产水稻,会把产量高一些、已经返青的禾苗打掉重来。杂交稻也是开始在那个时候强制试验的,制种时一斤可抵几斤,可仍然不划算。所以,现在说某某是水稻之父,只口不提全国人民中的一部分为此作出的贡献,我颇有微词。水利设施是年年要修的,某某湖曾修了若干年。有年冬天,青壮劳动力都去修湖了,剩下的就是妇女、小孩和老人来收割晚稻。
好在学生以学为主,顺带反点封资修、反击一下右倾翻案风、再来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。其他都好,最让我为难的是邓小平三字,刚在“毛泽东著作选读”上用红笔画个叉,过几天又变好了,而又过不了几天,还是要画个叉…… 批判大会上,老师报告中的“党内那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一词,得让我这个实心眼的人,揣摩半天,还不敢则声出来,生怕错了。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在公社的批判大会上,第一次喊“打倒王洪文”时,我仅嘴巴动了动,没有举手、也没有发出声音。
1970年代末期,我们生产队自发偷偷地分成了两个组,被发现而撤了一个队长;新队长上任伊始,意气风发、干劲冲天——还真落了一个俗套:天格外地晴。但好景不长,大人们的事小孩不知道,不知怎么弄的,又被分成了四个组——于是又撤了个队长。这下,安静了好长一段时间。再次看到丈量田亩时,大人偷偷地说:某某丘是我们家的。以后,不知是不知道、还是想不起来了,现在已不知那时这田到底分成功了没有,因为1978年下半年上高中了,在家的时间也少了。只记得在1981年,在党的号召下,必须要分田了,也真的又丈量了一次,真的分了。我并不高兴,因为一是社会主义的特点体现不出来了,二是做工时难得有故事听了、难得听到幽默了,少了许多的乐趣。刘少奇平反了,使人有点震惊和多少有点不习惯。
那也是一个牛鬼蛇神出笼的年代,我家就受了点损失。 1980年,一个地主说我爷爷利用职务之便(解放初期任乡长,我还见过象奖状一样的任命书)、住了他家的房子,要我们赔。找土改干部,应官司,最后总共需给他240元(我家和我两个叔叔每户80元),在那无处赚钱的年代,80元决不是一个小数目。气愤之余,写了几句:“忽来:多年未出笼,今日逞英雄;高禄在其身,何不去奉承”。那时,我已高中毕业,现在想起这几句有点好笑。
实际的情况是,解放前我家也是有房有山的,解放时的乡长也是谋不到私利的;仅是在土改时,土改干部不知怎么让我爷爷住到了没有办好没收手续的房子里(离原住处有两三公里),而自家的房子却给贫苦人家住了;后来打官司时,碍于情面,我们没有提出要自己的房子。
说得困了,一笔带过。以后是改革开放,然后是第一次严打、第一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,胡乔木(应当是这名字)《人道主义与异化》,学文件与提意见。随之,个人风光的年华一去不返(先是高考一再失利),终于明白自己不是块料,决定黑白两道均不进;努力做个卑微的好人而失败。之后是假
- 关于西门子 S7-200系列PLC在...
 [14619]
[14619] - 工控人的前途
 [15915]
[15915] - 别把犯践当真爱
 [6882]
[6882] - suv柴油车有哪些?
 [5095]
[5095] - 做技术支持每月拿多少薪水?
 [7539]
[7539] - 工控职场地图
 [17565]
[17565] - 一位热控人员的路程(绝对真实...
 [11112]
[11112] - 该不该学自动化专业?
 [15098]
[15098] - 我熟悉的那些工控论坛的男人...
 [9702]
[9702] - 老板为什么喜欢打小报告的员...
 [6400]
[6400]

官方公众号

智造工程师
-

 客服
客服

-

 小程序
小程序

-

 公众号
公众号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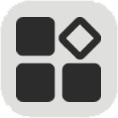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 工控网智造工程师好文精选
工控网智造工程师好文精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