乡愁是留不住的回声,捕捉不到的美丽。 点击:634 | 回复:1
眼看着,春节近了,外来务工人员开始一年一度的返乡热潮。故乡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心底最深的牵挂,最魂牵梦绕的所在。漂泊在外的游子说起故乡,话起故乡,故事总是那么长。近年来,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,经济高速发展,你我的故乡也早已换了模样,但它留给我们的年少记忆,情感里的那份不舍,无意触碰便在心底翻腾引我们无限遐想的过往,让我们不断回望。

乡愁,这个词有几分凄美。原先我不懂,故乡或儿时的事很多,可喜可乐的也不少,为什么不说乡喜乡乐,而说乡愁呢?最近回了一趟阔别六十年的故乡,才解开这个人生之谜。
故乡在霍山脚下。一个古老美丽的小山村,水多,树多。我家院子里长着两棵大树。一棵是核桃,一棵是香椿,直翻到窑顶上遮住了半个院子。香椿炒鸡蛋是一道最普通的家常菜,但我吃的那道不普通。老香椿树的根不知何时,从地下钻到我家的窑洞里,又从炕边的砖缝里伸出几枝嫩芽。
我们就这样无心去栽花,终日伴香眠。每当我有小病,或有什么不快要发一下小脾气时,母亲安慰的办法是,到外面鸡窝里收一颗还发热的鸡蛋,回来在炕沿边掐几根香椿芽,咫尺之近,就在锅台上翻手做一个香椿炒鸡蛋。那种清香,那种童话式、魔术般的乐趣,永生难忘。
这次回村,我站在老炕前叙说往事,直惊得随行的人张大嘴合不拢。而村里的侄孙辈也如听古。因为那两棵大树早已被砍掉,只有旧窑在,寂寞忆香椿。

出了院子,大门外还有两棵树,一棵是槐树,另一棵也是槐树。大的那棵上面有鸟窝、蛇洞,还寄生有其他的小树、枯藤,像一座古旧的王宫。爬小槐树,是我们每天必修的功课。隐身于树顶的浓阴中,做着空中迷藏。
夏天的一个中午,正是日长人欲眠时,突然老槐树上掉下一条蛇,足有五尺多长,直挺挺地躺在树荫中。一群鸡,虽以食虫为天职,但还从未见过这么大的虫子,一时惊得没有了主意,就分列于蛇的两旁,圆瞪鸡眼,死死地盯着它。双方相持了足有半个时辰。这时有人吃完饭在河边洗碗,就随手将半碗水泼向蛇身。那蛇一惊,嗖地一下窜入草丛,蛇鸡对阵才算收场。现在,就是到动物园里,也看不到这样的好戏。
出大门外几十步即一条小河。流水潺潺,不舍昼夜。河边最热闹的场景是洗衣。印象最深的是河边的洗衣石,有黑、红、青各色,大如案板,溜光圆润。这是多少女子柔嫩白净的双手,蘸着清清的河水,经多少代的打磨而成的呀。河边总是笑声、歌声、捶衣声,声声入耳。现洗好的衣服就晒在岸边的草地上,五颜六色,天然图画。
我们常在河边的青草窝里放羊,高兴时就推开羊羔,钻到羊肚子下吸几口鲜奶,很是享受。清明前后,暖风吹软了柳枝,可退下一截完整树皮管,做成柳笛,呜哇呜哇地乱吹。大人不洗衣时我们就在这洗衣石上玩泥,或坐上去感受它的光润。可惜,这情景永不会再有了,村里的三条河全部干涸,连河床都已荡平,树也没了踪影。洗衣歌、柳笛声都已成了历史的回声。

忆童年,最忆是黄土。村里人土炕上生,土窑里长,土堆里爬。黄土是我的襁褓,我的摇篮。农村孩子穿开裆裤时,就会和泥。一群孩子,将胶泥揉匀,捏成窝头状,窝要深,皮要薄。口朝下,猛地往石上一摔,泥点飞溅,声震四野,名“摔响窝”。以声响大小定输赢,以炸洞的大小要补偿。输者就补对方一块泥,就像战败国割让土地,直到把手中的泥土输光,俯首称臣。孩子们虽个个溅成了泥花脸,仍乐此不疲。村庄若没有了孩子,就没有了笑声,也没有人会去让泥巴炸出声。
从春到夏,蝉儿叫了,山坡上的杏子熟了,嫩绿的麦苗已长成金色的麦穗,该打场了。场,就是一块被碾得瓷实平整,圆形的土地,是粮食从地里收到家里的最后一道程序,再往下就该磨成面,吃到嘴里了。割倒的麦子被车拉人挑,铺到场上,像一层厚厚的棉被,用牲口拉着碌碡,一圈一圈地碾压。孩子们终于盼到一年最高兴的游戏季,跟在碌碡后面,一圈一圈地翻跟斗。我们贪婪地亲吻着土地,享受着燥热空气中新麦的甜香。
一次我不小心,一个跟斗翻在场边的铁耙子上,耙齿刺破小腿,鲜血直流。大人说:“不碍,不碍。”顺手抓起一把黄土按在伤口上,就算是止血了。至今还有一块疤痕,留作了永久的纪念。也许就是这次与土地最亲密的接触,土分子进入了我的血液,一生不管走到哪里,总忘不了北方的黄土。现在机器收割,场是彻底没有了,牲口也几乎不见了,碌碡被可怜地遗弃在路旁或沟渠里。有点“九里山前古战场,牧童拾得旧刀枪”的凄凉。
没有了,没有了。凡值得凭吊的美好记忆都没有了。只能到梦中去吃一次香椿炒鸡蛋,去摔一回泥巴、翻一回跟斗了。我问自己,既知消失何必来寻呢?这就是矛盾,矛盾于心成乡愁。历史总在前进,失去的不一定是坏事,只是有一种温馨的淡淡的哀伤,这种感觉如在古老悠长的雨巷里“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。”乡愁是留不住的回声,捕捉不到的美丽。
楼主最近还看过
- 工业机器人培训
 [206]
[206] - 请教阻容吸收器用法
 [1036]
[1036] - 想学PLC,应该怎么入手
 [592]
[592] - PLC发展好还是ARM发展比较好...
 [197]
[197] - 步进驱动器在运行时有时会出...
 [252]
[252] - 毒舌就是这样炼成的~
 [363]
[363] - 阿胶干红,挺起民族的脊梁向世...
 [190]
[190] - 如果您企业仍然在AGV上犹豫不...
 [193]
[193] - 电气部门人员流失怎么办
 [205]
[205] - 博图软件打不开梯形图是怎么...
 [236]
[236]

官方公众号

智造工程师
-

 客服
客服

-

 小程序
小程序

-

 公众号
公众号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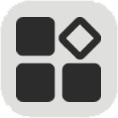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 工控网智造工程师好文精选
工控网智造工程师好文精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