浮萍人生——写给我的不惑之年《原创》 点击:8172 | 回复:224
人说三岁看老,说一个人的一生能从你刚刚走进这个世界,根据你的爱好,你的举止和行为就能看出端藐,虽有点武断,颇有一点道理。感觉自己像所有未成年孩子一样,都有一颗好奇的心,喜欢拆解东西,尤其是电器,那时也没什么象样的电器,家里好象就有白云黑土结婚是买的那样家电。后来发现生产队的拖拉机灯很亮,也是个玩点。几个人就拆了几个去玩了,恰逢村里装电,感觉25W的白炽灯总不如拖拉机上的小泡亮,何不拿来一试。那次的试验差点没造成大的遗憾,接通以后就是蓝光一闪,啪的一声,灯泡炸的粉碎,所幸没伤着自己。这就是无知者无畏吧。后来比较高级点的玩具就是小型直流电机了,五年级时做出了第一个风扇,初中时功课落了很多,混日子这个词用在那时最恰当不过了,迷迷澄澄的童年就这样过去了,所幸玩的过程中自修了高中物理,知道了能量守恒,知道了电磁转换,虽然只是看点皮毛,毕竟为后来从事的工作积累了一点东西,后来在一家职业学校学到了一点最基本的可以换饭吃的东西。
青年时期是个不安分的年龄,和大部分年轻人一样涌入了打工者的大潮。二三月份,春寒料峭,还没脱掉棉袄,和我们一个村的老乡来到那个中国北方很有名的村子—大邱庄。那天并没有找到要找的人,晚上吃了几个烧饼,如果再住旅馆可能连回去的车票都没有了,在街上溜达吧还怕叫人家当盲流给抓了,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呆一会吧。在这个漆黑寒冷的夜里,我们生起一堆篝火御寒, 并发誓谁也不要把此事说出去,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,但愿第二天能够顺利,不然就只有打道回府了。第二天真的很顺利,找到工作后发誓一定干好,一连几天都在刷防绣漆,铁红色的防锈漆把脸上手上都染红了,还没有汽油洗,像刚下火线有幸活下来的勇士。终于在第四天的时候,这个比我大好几岁的榜大腰圆的老乡提出了撤退,并且怎么劝都不行。把我一个人仍到那里回到了老家,对我的母亲说:你儿子在那受苦了。 我母亲说那我儿子能受你为什么不能呢?他哑口无言了。那一刻我想我的母亲是自豪的,因为他的儿子没有叫困难压倒。那时很累,在一家化工厂,建厂时期很多活是重体力劳动,虽然领导看本人身材小一些还是有些照顾的,但也是吃不消,毕竟从小没参加过劳动。那时的饭量是现在的三倍,每顿可以吃五分钱一个的大馒头三个,至于菜那就只能叫菜了,好不容易熬到了投产,整天跟氯气打交道,那段时间的生活真的是很灰暗,但强烈的好强心还是让自己坚持了下来,别人能成自己就能成。当时厂里有个仪表室,那个管仪表的是考了驾照刚下来白本,正在等红本,红本下来之后人就走了,仪表室有个空缺,副厂长不知怎么就看上我了,我便理所当然的成了一名仪表工,负责维护全厂的自控仪表,仪器,压力表等事宜,在一段时间的努力下终于小有成效,恢复了一部分停用的自动供水系统,被电业科注意到了,科长就问了:怎么样,想当电工吗?当然是想了,厂长一看我工作天天也很轻松,加点工作量也是应该的。大手一挥,去吧,过去给他们当个班长,好好干啊!手下有两个年轻的和一个老头,连个接触器都接不了怎么干呢?请教吧,这老头一看我老人家连个接触器都不会,还来给他当领导,还很谦虚不耻下问,心里还不一定想我是哪个领导的远房老伯伯呢,第二天就打包袱卷走了. 一 段的坎坷,终于归入了正途,那段时间里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和最得意的时光,永远不能忘记我几十年人生旅途中帮助过我的贵人,他们让拥我有了一个自己热爱的职业.当我在十字路口徘徊时向我指了一下方向,虽然这对于他们也只是举手之劳.或是工作需要.但我一直有一个心愿,那就是能有一个机会向他们表明我的谢意,是他们不经意间一个小的安排改变的我的人生.受人滴水之恩虽不能报以涌泉,但也应铭记终生.
和所有人一样,工作关系就是天下无不散之宴席.结束了化工厂的工作,蹋入特钢厂,接触了大型起重设备,高压电器,电弧炉,见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工业电子.工作还算得心应手,平时的工作倒不紧张,但到了出钢的时候就很关键了,几十吨的起重机吊起钢包出现故障,需要以飞快的速度到现场, 并在十分种之内处理完毕,否则钢水就变成钢砣子了,全厂人一个月的奖金也功亏一篑.白天怎么都能行,到了夜班睡的迷迷糊糊的马上投入战斗也是件不容易做到的事,其实夜班是不允许睡觉的,没办法老家伙是没人管的了的.也就是在这几年里患上了神经衰弱,睡觉很轻,稍有声响就的惊醒,心理扑腾一下.也是那时理解了什么是职业病.不过,必须承认,那几年是风平浪静的几年,有上班,有下班,歇班时无聊转一转,或是练练书法.学习学习,找点闲情逸致.92年是抓禹作敏的那年,感觉有点像是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,社会面貌焕然一新,外工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有所提高.挣到了400元的工资就是全厂的高工资了.那时的物价相对很便宜,每月花掉200,后来挣到了600,花掉300,争到了1000,花掉500,感觉总是在玩打对折游戏.干了这么多年还是囊中羞涩.平时都是沉侵在:你们都是技术骨干,都是人才,是有很光明前途的这些甜言蜜语中,感觉能挣到高薪真的是很遥远的,反正还年轻,那时有句话叫挣钱不挣钱不在头三十年,老了老了拉几吧倒了.真的是当时的写照.几年的漂泊感觉有些累,有些想懈怠的意思,工作的新鲜感没有了,感觉这个世界上就那么几样电器,学的够多了,够用了,再多的工业电器无非像人的衣服嘛,如出一辙,就是裁剪方式和做工变了变.什么公式定律术语都是不实际的东西,不能当饭吃,只能理论上说一说.治头痛就是安脑宁,发高烧就是安乃劲.没有后来的工作就不能理解当时的狭隘,闭塞,自大.无知. 忽然间的心血来潮,不干了,回家搞一点小生意怎么也能糊口的.说干就干了,就像对工作的无知一样又蹋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,换来的就是抛干有限的积蓄和灰头土脸.明白了一个人是不能贸然蹋入一个陌生领域的.一年后,原单位领导听说了我的情况,找到我们在销售科的一个哥们:不行叫小牟回来吧,在家也干不好,看能行打个电话联系一下.一打电话老厂长就说了:今年有点特殊情况,你看你在家也不很好,如果你愿来我出1400元的工资,如果不能来就当给我帮帮忙,把车给我开起来,咱们再说,行吗. 那就来吧,工资还能说的过去啊.说的好听一点叫请,说的不好呢单位愿意用我啊.这回是孤家寡人一个人来的,回到老地方,见到老人,穿新鞋走老路啊.一切都轻轻松松过去了,一切还的从头在来.两年后这个工作了五六年的单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,面临倒闭,只好另寻他路了。以前来过胜芳一次,感觉不很好,满大街的油鬼子,穿工作服到处跑,一下雨到处是泥,一条大街从这头走到那头就找不到个厕所,和大邱庄井然的秩序有天壤之别,好赖大小厂有个浴池,工人上班一身,下班一身.这倒好工人都是油鬼子,老板都是爆发户.没办法,怎么也的生活,怎么也的求职,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一个小的不能在小的厂子,工资再低也的干,我要进入这片天下就要先熟悉一下情况,争取能学到高频技术,找一份还能象样的月薪,干吧,一切又开始了,刚去的几个晚上,一个人在小吃部里斟上一杯一块钱的白酒,来一盘一块钱的菜,昏暗的灯光下自斟自饮,外面下着小雨,在这凄风苦雨的夜晚,想到了林冲夜守草料场,想到了雪夜上梁山。周围虽然都是熙熙攘攘的人。感觉就是跟自己无缘的另外一个世界。想到自己三十几岁还独自漂泊到这个人地两生的北方小镇,在这个不能再小的厂里挣着不能再少的薪水,第一次感到孤独,无助,无奈,委屈,眼泪不自觉的落进酒杯。男人—就是很难的人,这个词含义太广,包含太多的责任.义务.需要一生为捍卫它的尊严而奋斗。
熬过了一个艰难的冬天,春节后找到了一分新的工作,工资虽还不能尽如人意,但毕竟是芝麻开花了。最重要的是我在这个大单位里,见到我生平未见的高频,微机锯,欧陆,轧机传动。在这一年里,过多的设备和故障率,使自己能 接触到比平时别的小厂高五倍的维修量,再拿出五倍的热情,对于收获自己颇为自豪,让自己
我认真的看下来了,真好!
经历都相似,只是没有你的文采好,说不出心里的感受,小时候你试验的是小灯泡,我试验的是电石灯,装着水与电石的玻璃瓶爆炸啦,万幸没有伤到,也没敢说出来,再后来拆坏了3只机械手表,收音机、黑白电视机......自学电子、电器修理,参加工作----专业不是自己想的,只能是自己偷着学习。
一直相信:机会是自己创造的!
公司进口一套设备,因春节将至厂家没有人安装,我大胆安装好了----以后开始进入电气专业----
后来觉得与其给别人打工不如给自己打工,什么也不要啦,一狠心辞职走人----
经历过艰辛、努力、彷徨-----终于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。
相似的感悟
第一次感到孤独,无助,无奈,委屈,眼泪不自觉的落进酒杯。男人—就是很难的人,这个词含义太广,包含太多的责任.义务.需要一生为捍卫它的尊严而奋斗。
奋斗的人生是没有遗憾的,不管你是否拥有财富,你都拥有一个无悔的人生。几十年的奋斗,虽然还是接近于囊中羞涩,但感觉自己还是个成功的男人,在上一辈那里得来的只是几间基本已不能住人的祖屋,我用自己的双手为家人在这个远离家乡的异地遮起了一个小天地,让他们像所的女人,所有的孩子一样无忧无虑,享受生活,虽然我并没有让他们享有富贵。我时常说,男人挣钱.顾家.心里有老婆孩子那就是好男人,对生活不要奢望太多。这么多年风也罢雨也罢,曾经的辛酸,曾经的苦难,都是人生宝贵的积淀,让你拥有更多的能量面对困难,战胜困难。
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事业会有高峰也会有低谷,当你走如低谷的时候,就意味着不远的地方就是高峰,当你处在高峰的时刻,事业会出现低谷也是必然的,就像每天的太阳一样有规律。盛极必衰.否极泰来,在易经中的解释为宇宙及人生中两种截然相背反,截然相对峙的品性和势力的消长,此消彼长,此长则彼消。
四十年人生,二十年的飘荡,犹如一根浮萍,有根——却在漂浮。家——是心灵疲惫时的歇息之地。老婆孩子——漫长人生旅途的搭伴。父母——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缔造者,从把你养大成人那一刻起,你就背上了对他们永远的亏欠。朋友——你心情苦闷时的倾诉者,他百无聊赖时的倾听者,事业上的互助者。
很好!
继续努力!!!
- 磁悬浮和双滚珠的风扇哪个好...
 [6995]
[6995] - 我熟悉的那些工控论坛的男人...
 [9702]
[9702] - 三菱3UPLC怎么和台达ASDA-B2...
 [7677]
[7677] - 台达的PLC DVP-32EH ERROR闪...
 [6437]
[6437] - 原创:工控书法论坛
 [12564]
[12564] - 让我们来玩一个游戏
 [11038]
[11038] - 宝钢综合自动化技术的现状和...
 [5895]
[5895] - 徒弟与师傅--烧坏PLC的感觉
 [4875]
[4875] - 现在工控行业的工资大概多少...
 [23697]
[23697] - 请收到“工控TOP 10”光盘的朋...
 [6221]
[6221]

官方公众号

智造工程师
-

 客服
客服

-

 小程序
小程序

-

 公众号
公众号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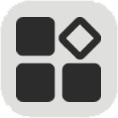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 工控网智造工程师好文精选
工控网智造工程师好文精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