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南与路透社记者对话录 2 点击:198 | 回复:3
发表于:2008-08-22 20:40:32
楼主
路透记者:民主的问题,你的判断是什么?
司马南:我愿意坦白自己的判断:中国社会今天也许并不急着实现“票决式民主”。理由很简单,即使中国政治一切按照美国方式来,似乎也不必如此着急,今天美国的所谓民主尚为“代议制”,而非票决制,非直选式,贵国今天还在“君主立宪制”阶段,中国为什么要比美国还美国?
《南方周末》和《南方都市报》为代表的南方报系,他们主张在中国进行激进的变革,鼓动痴迷的读者《相信选票的力量》(南方周末时事评论员,著名杂文家鄢烈山先生时评标题)。问题是美国人自己,好像并不那么相信选票的力量啊,因为他们知道选票的程序设计更重要。事实告诉我们,谁当总统,并非选票就可以决定。如果按鄢烈山的信念,2000年那一次,当选的美国总统应该是戈尔先生,而不应该是布什先生。布什在其亲兄弟当州长的佛州只比戈尔多537张选票,大选难产36天。最高法院竟然判布什赢得佛州选举,好家伙,该州27张选举人团的票都归了布什。就这样,布什仅比戈尔多出5张选举人团的票,可是全国你少了54万张选票啊!分明是输了选票嘛。但是大法官判定布什当选,最后区区几百人的“选举人团”的票才是有力量的,大法官的票更有力量。鄢烈山文章的标题应该改为《相信选举人团的票有力量》,《相信大法官的票更有力量》(笑)……问题是大法官的产生并非民主。
南报的人可能不了解事实,也可能并不愿意传播事实,更大的可能是为了表达上的简便和快意,简单的带有反叛意味的解构式的口号,总是有利于调动适应其报纸口味多年的读者的热情。
即使我们完全照着西方的民主宪政理论来实行民主,选票的力量也必须借助法治的力量才得以发挥作用,而民主与法治均需要社会一定的条件。当今世界上,很难举出例子证明在工业化现代化没有完成之前,实行美式民主成功转型的国家,而实行美式民主把国家搞得一团糟的例子则比比皆是。
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工业化尚未完成,信息化社会突至,人口众多资源瓶颈限制严重,贫富差距拉大腐败情况严重社会矛盾激增,政府和执政党正在勉力为之全力以赴应对时艰。在这种情况之下,鼓动激进的变革,当然鼓动者本人容易在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当中产生明星般的影响力,但是社会结果会怎么样呢?人们完全可以想见。结果之一便是产生一批赚取眼球的“政治明星”——贺卫方已经被誉为最敢讲话的“中国法学界的良心”,鄢烈山已经被一些人誉为“最敢说话的评论家”,南报则被誉为“中国最敢说实话的报纸”。他们的所谓“敢说”,无非说明了三个问题:其一,中国社会今天的“言论自由度”确实大的令人惊讶;其二,证明了报纸言论对社会不负责任,进而无须对言论后果承担责任;其三,也许还证明了另外一点,哗众取宠的激进主张,与报纸发行量、广告额和个人的知名度正相关。
请允许我再表达一种判断:不知道先生您怎么看,在中国实行激进变革的政治主张,以崇拜选票力量为先导,以对政府的不信任讨伐为目标,附之以非理性情绪蕴藉的特性,旗帜上大大地写着“普世价值”,而所谓普世价值通过媒体的预热宣传已然获得了道德位势,这是一个舆论的变形金刚……我希望自己已经表达出了一种深深地忧虑。一任其宣泄下去,后果是可怕的,一任其横行下去,已经产生警觉性的人是失职的。您不是问我事件的意义吗?战场上狙击手的作用,或房子着火之后消防员的作用,可能就是意义吧。显然,反对普世价值传销,拆穿他们的谎言,我们是被动的,不得以的,至多是一种制衡的保守的力量。
路透记者:您觉得媒体缺少鲜明的保守的观点?
发表于:2008-08-22 20:41:27
1楼
司马南:是的。对于某些媒体错误倾向和极端观点,缺少旗帜鲜明的批评,好似不敢“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”(毛泽东语)。对几个以文学家、历史学家、法学家、哲学家面貌出现的,事实上要么是良心大大地坏了,要么是大脑出了问题。对社会有害的极端分子,我们的舆论过于宽容,好像好人反倒怕坏人一样,您在中国没有这种感觉吗?
所谓好与坏的标准,简单得很,就一条,看其怎样对待民族和国家利益,看其到底是维护捍卫国家的根本利益,还是损害削弱国家的根本利益。您可能听到这样的说法不明究竟,但是,假如今天这番话被一些网友听见,并不费力就可以列出一个名单来。今天的中国,思想阵线清晰分明的很。关于普世价值的理解,若说有难度,对外国记者来说,可能就难在这里——背景投射过于复杂,许多讨论话里有话,所以先生应该学会听话听声,细心捕捉弦外之音。
路透记者:慢慢学习吧。那么,你的文章为什么影响那么大?
司马南:大吗?只对一部分人有触动而已。我对《南方周末》的批评,其实就是在自己博客中贴了几篇文章,全世界每天生产多少博文,谁看啊?为什么贴了这么几篇文章,会有一些反响呢?一些人为什么这么急迫做出一系列反应呢?并非我这个人怎么样,我想可能是因为文章说出了一部分人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,在同道者哪里引起了共鸣,而在另外一些人那里造成了惊悚效果。
他们说我保守,我姑且承认,这比其他难听的话还好一点。有人骂我为“***的鹰犬”,说我是“***的狗”,“**专制的帮凶”(笑)那好,这恰好证明,中国今天需要这么保守一点的力量。用“保守力量”这个词,对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来说,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些(笑),激进的卢梭是法国人啊。在今天,保守往往意味着负责任,意味着理性,意味着保持平衡小步快走,而不是中国股市大幅震荡,走钢丝儿或休克疗法。
中国的变化已经够快的了,他们还嫌不够快,他们可能天生适合当赛车手,如韩寒那样(笑)。今天这种激进的“票决式民主”的主张,这种“选举迷信”的宣传,是个挺可怕的事情。我这个年纪的人是经历过文革的,您作为中国通,想必对中国非常了解,但您没有体会过文革。那时候,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大辩论,无数的组织(政党)揭竿而起,毛主席绝对权威尚在,社会也是乱得可以。那是一种大民主,后现代意义上的大民主啊,但是,有序的社会承受不起。所以30年来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文革的反思和讨论,对毛主席肯定的正面评价,因此而打了折扣。经历过文革的人,很少有人会赞成激进式的政治变革,打着普世价值旗号的激进的政治变革同样不受待见。
关于普世价值,我基本看法是,普世价值“这个词”当然存在,对其语言学意义上的诸多阐发探微我均赞成。与其接近的“共同价值”、“基本价值”、“基础价值”、“多数人价值”、“基本共识”等等也应在探究之列。本人对“社会语言学”很有兴趣,那个“转换生成流派”的乔姆斯基这个人很好玩,他自己的学问在不同学科里“转换生成”且自成“流派”,确有真知灼见,《南方周末》关于普世价值问题应该去问问乔姆斯基(大笑)……对,那是个著名的美国左派学者。
发表于:2008-08-22 20:42:04
2楼
总之,“普世价值”到底有没有?可以各抒己见,进行深入的讨论,其作为议题我没意见,当然不会反对。但是,既然你来中国传销它,公开忽悠这么久了,对“普世价值”前世今生,得允许我们问几个为什么吧。“普世价值”从何而来?怎么来的?谁介绍来的?我们知道“价值”概念源自于有用性,是经济学的范畴;“价值观”是人们对价值问题的看法,是主观的,基于主体判断而产生,与特定的历史文化制度相联系。而今一种“价值”突然横空出世,且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,气势如飞虹,天马自行空,啪地一个变形金刚亮相(笑),就弘论普世强行普世,多问几个为什么应该不为过吧?
“普世价值”,它是由什么人以什么方式决定出来的?是南报人相信的推崇的主张的“票决”出来的吗?谁参与了投票?投票程序由谁设计的?法学家常常强调,“法律正义的前提是程序正义”,“法律的历史就是程序的历史”。既然宣称“普世”,那便“放之四海而皆准,通贯古今而畅行”(笑),您笑什么?您了解?前一句话是我们毛主席的专用词,讲的是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,今天中国共产党说法已经改变了。那么,整个世界通过什么形式使某一种价值获得了普世价值的地位呢?
有人说“人有共性,人性就是普世价值,司马南不承认普世价值是自况非人”(笑)。说这种话的人书呆子而已,呆气很重,自可一听了之。《南方周末》作为国内“普世价值”传销大户,未必会接受这种胡乱帮倒忙的行为。
(司马先生与路透记者谈话第一部分,李丽茹根据录音整理,未完待续)
热门招聘
相关主题
- 工控行业究竟工资有多高
 [5619]
[5619] - 求助:谁有NEC工控软驱
 [27315]
[27315] - 关于气动阀门定位器的放大器...
 [6512]
[6512] - 用电位器控制三菱伺服MR-J2S...
 [7051]
[7051] - 磁悬浮和双滚珠的风扇哪个好...
 [6995]
[6995] - 求助:变频器辐射是否对人有害...
 [5682]
[5682] - 低薪危机(转载)
 [8081]
[8081] - 年薪30万工控老鸟成长之路
 [4815]
[4815] - 图文:『工控美眉』◆◇恋恋生活秀...
 [16121]
[16121] - 100个人有96个会答错的题目
 [7245]
[7245]

官方公众号

智造工程师
-

 客服
客服

-

 小程序
小程序

-

 公众号
公众号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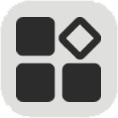









 工控网智造工程师好文精选
工控网智造工程师好文精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