孜然--“自然” 点击:768 | 回复:6
发表于:2008-05-09 13:43:16
楼主
孜然--“自然”
2007年05月28日 12:25:20 稿源: 新疆经济报 图/文沈苇 发表评论

孜然,总是一边开花,一边结果,成熟时,田野上飘着奇香。孜然,对于新疆人而言是熟悉的,然而又是陌生的。比如,很多人不知道:新疆孜然为伊朗型,品质介乎印度型和土耳其型之间;孜然这种波斯香料是什么时候传入西域的;托克逊县的孜然是生长在零海拔之下的;新疆一个偏远的维吾尔族村庄的孜然已经走出国门了;新疆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2000年开始对孜然进行攻关研究,这在国内尚属首次……——编者
香料滋润人们的生活,使生活变得更为丰富多彩。
——(英)马斯格雷夫:《改变世界的植物》
没有一个新疆人的生活是可以和孜然毫无关系的。孜然渗入到新疆饮食的方方面面。烤肉就不用说了,没有孜然就没有新疆烤肉。烤全羊、烤包子、薄皮包子、馕、原始抓饭、维吾尔药茶、不沾小料涮羊肉等也都普遍使用孜然。作为新移民的我,出于对新疆美食的热爱,也自然爱上了孜然的味道、孜然的异香。
在新疆,孜然的需求量和销售量是惊人的。在南疆县级以上的农贸市场,大多数调料铺的孜然销售量以吨计算。据我在托克逊县农贸市场的调查,这家市场共有十几家调料铺,每个铺位年销售孜然在两吨以上。仅这一个市场,一年的孜然销售量就在30吨左右。孜然是当之无愧的新疆第一调料。所谓的新疆味道,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孜然味道。想象一个人,在新疆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,他的身上、他的心灵以及他的气质,就会散发出这种独特的味道。
作为新疆人的一员,我使用孜然,消费孜然,爱着孜然,却对这种植物缺乏必要的了解。在延时20年之后,我才第一次看到长在地里的鲜活孜然。
此时是5月上旬,我站在托克逊县夏乡色日克吉勒尕村的大片孜然地里。这片孜然地有数百亩,是成片单播。但更多的孜然套播在棉花地和玉米地里。此时的孜然,一半在开花,一半开始结果。细小的紫色花朵缀满枝头,随风摇曳,闪现在一望无际的绿色中。村民们在为孜然锄草,近旁的麦子在静静抽穗。
记得在乌鲁木齐时,孜然专家张谦告诉我孜然开花的特点是“无限花序”。也就是说,每一株孜然都在尽最大的努力,使自己的复伞形花序无限繁衍、开放。这几乎是对自我极限的一次挑战。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,孜然开花就像节日的焰火在夜空无限盛开。所不同的是,礼花过后是空洞的夜晚,孜然花开过则是芬芳的、丰收的原野。
我蹲下身子,仔细而入迷地观察一株正在开花的孜然。英国诗人丁尼生说,当你从头到根弄懂了一朵小花,你就懂得了上帝和人。面对一株孜然,我也想说同样的话。
孜然的学名为枯茗(CuminumcyminumL.),也叫安息茴香、野茴香,为伞形花科孜然芹一年生草本植物。它的原始产地在北非和地中海沿岸地区。
目前世界范围内种植孜然主要是印度、伊朗、土耳其、埃及、中国和前苏联的中亚地区,基本上分布在从北非到中西亚的干旱少雨地区。由于孜然是制作咖喱粉的重要原料,印度是世界第一孜然大国,它的西部地区普遍种植大粒子孜然,品种也与别的国家有所不同。
新疆孜然为伊朗型,品质介乎印度型和土耳其型之间。它是通过丝绸之路从波斯传入古代西域的,与胡椒、没药、安息香的东传有着大致相同的线路。
新疆曾经是我国孜然的唯一产区。主要分布在东疆的吐鲁番、托克逊县及巴州的焉耆回族自治县,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县、沙雅县,喀什地区的岳普湖县、疏附县,和田地区的墨玉县、皮山县等,北疆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也有少量栽培。2005年种植面积达70万亩。近几年从新疆引进后,内蒙古、甘肃和云南也有了一定数量的种植,但新疆的种植面积仍占到全国的80%以上。
孜然不仅是新疆最重要的食物调料,也是维吾尔药中必不可少的药材。药理表明,孜然果实及挥发油有驱风、兴奋神经、健胃、抑菌作用。主治胃寒呃逆、食欲不振、腹泻腹胀、小便不利、血凝经闭等。孜然飘香的街区
在乌鲁木齐市二道桥、喀什老城、和田大巴扎等一些孜然飘香的街区,孜然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一座城市的门。借助孜然的香味和感官的陶醉,我们似乎能一下子抓住城市的灵魂。因此,我称这些地方为“孜然街区”。它们常常是城市最古老的部分,是热闹的商业饮食区,同时也是最具魅力、最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。
不少旅行者是通过气味来发现并喜欢上乌鲁木齐的。这就是这座城市大街小巷到处弥漫的烤羊肉串、各色馕饼、热腾腾抓饭的香味,尤其是孜然这种 “首席”香料的气味。它先是抓住你的嗅觉,继而征服你的胃口。就像普鲁斯特笔下的小玛德莱娜点心,多年之后当你在别的地方闻到类似的气味时,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在新疆旅行时度过的难忘时光。
作为乌鲁木齐最著名的维吾尔族聚居区,二道桥是中亚美食博览中心,是一席流动着色彩、音响、气味的盛宴。当然,我更喜欢那个 “沿街为市”的老二道桥,街上人头攒动,烤肉炉烟雾缭绕,建筑(尤其是几座木结构的清真寺)有时光的沧桑感,给人一种踏踏实实、真真切切的“在人间”的感觉。而改造过的二道桥,尽管洋气了,现代化了,却多了些刻意的、香艳的色彩,少了些原初的朴素和世俗化的亲切。假如有一天,烤肉炉和馕坑纷纷向室内转移了,古老的街区将变得面目全非,留下的只有叹息了。
在二道桥,孜然独特的芳香来自烤肉炉、馕坑,来自快餐店、宴会厅,来自调料铺、药材店……孜然无处不在,它的芳香四处飘游、弥漫。是孜然激发了维吾尔饮食的特点:质朴、浓郁、热烈。这种特点与新疆大地呈现的气质和风格是一致的。一个地方散发的气味也会打上这片地域的印记。
我不知道孜然这种波斯香料是什么时候传入西域的,但回顾人类的历史,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,对异域香料的需求和热爱由来已久。马可·波罗在描述13世纪的杭州时说,这座城市一天就运来了5吨波斯胡椒。他还说:在中国南方,有钱人可以享用好几种香料腌制而成的肉,下层民众的盘子里却只能嗅到大蒜味。
“香料滋润人们的生活,使生活变得更为丰富多彩:它是药品,可以治病;是调料,使饭菜更加可口;是香水、润肤剂和春药,可使人心旷神怡。” (马斯格雷夫: 《改变世界的植物》)
爱德华·谢弗在 《唐代的外来文明》一书中指出,几乎所有的香料都经历了一个从神坛走向世俗的过程。古时候人们常常在祭祀用的酒和肉中加入香料作为调味品,目的是为了防止祭品腐坏,增加祭品对于神的吸引力。后来,香料渐渐世俗化了,走下了神坛,搬上了贵族的餐桌,甚至还进入了寻常百姓人家。
我不知道孜然是否也经历了从神坛到世俗的演变。但细究孜然的风格特点,它的身世与沉香、没药显然是不一样的。它绝对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那种。它的芳香浓郁而热烈,紧贴着大地。其天生就属于民间,属于大众,属于世俗生活的光阴和食谱。
二道桥,孜然焚香的街区。一个二道桥的烤肉炉就是一个世俗的、肉感的、烟雾袅袅的 “焚香炉”。 “一串肉在火上尖叫/就是一只羔羊在火上尖叫,是一百只羔羊在火上尖叫/多少只羔羊已葬身人的口腹之坟!” (《混血的城》)
维吾尔族人称烤肉为 “喀瓦普”,是对烤羊肉串、烤全羊、馕坑烤肉的统称。当然还应该包括南疆更为原始的烤肉:立体烤肉 (架子烤肉)和火埋羊肚子烤肉。在新疆城市街头,烤肉是最为普及的风味快餐。一个烤肉炉,一点细盐、孜然、辣椒面,就能烤出美味可口的羊肉。滋滋冒油的肉串,孜然的香味,还有烤肉师傅的吆喝声,成为一幕幕生动的街景。三五朋友,围桌一个烤肉炉,喝着地产的啤酒,海阔天空地聊着,不亦乐乎?不亦快哉?
值得一提的是,南疆和田等地的一些烤肉师傅从来不用辣椒面,只用孜然和盐。因为在他们看来,辣椒面既改变了烤肉的风味,又能掩盖羊肉的不新鲜。为了烤肉的纯粹,他们只信任孜然和盐。
一个烤肉炉不仅用来烤羊肉串,还能用来烤羊排,烤羊杂、烤羊肉丸子、烤牛肉、烤鸡肉、烤鱼、烤玉米、烤蔬菜,等等。一个普普通通的新疆烤肉炉,轻而易举就能烤出一席街头盛宴。
烤,古称炙,作为烹饪法的一种,有着悠久的历史。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2200多年前的有关饮食的遗策中,就有 “牛炙”、
2007年05月28日 12:25:20 稿源: 新疆经济报 图/文沈苇 发表评论

孜然,总是一边开花,一边结果,成熟时,田野上飘着奇香。孜然,对于新疆人而言是熟悉的,然而又是陌生的。比如,很多人不知道:新疆孜然为伊朗型,品质介乎印度型和土耳其型之间;孜然这种波斯香料是什么时候传入西域的;托克逊县的孜然是生长在零海拔之下的;新疆一个偏远的维吾尔族村庄的孜然已经走出国门了;新疆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2000年开始对孜然进行攻关研究,这在国内尚属首次……——编者
香料滋润人们的生活,使生活变得更为丰富多彩。
——(英)马斯格雷夫:《改变世界的植物》
没有一个新疆人的生活是可以和孜然毫无关系的。孜然渗入到新疆饮食的方方面面。烤肉就不用说了,没有孜然就没有新疆烤肉。烤全羊、烤包子、薄皮包子、馕、原始抓饭、维吾尔药茶、不沾小料涮羊肉等也都普遍使用孜然。作为新移民的我,出于对新疆美食的热爱,也自然爱上了孜然的味道、孜然的异香。
在新疆,孜然的需求量和销售量是惊人的。在南疆县级以上的农贸市场,大多数调料铺的孜然销售量以吨计算。据我在托克逊县农贸市场的调查,这家市场共有十几家调料铺,每个铺位年销售孜然在两吨以上。仅这一个市场,一年的孜然销售量就在30吨左右。孜然是当之无愧的新疆第一调料。所谓的新疆味道,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孜然味道。想象一个人,在新疆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,他的身上、他的心灵以及他的气质,就会散发出这种独特的味道。
作为新疆人的一员,我使用孜然,消费孜然,爱着孜然,却对这种植物缺乏必要的了解。在延时20年之后,我才第一次看到长在地里的鲜活孜然。
此时是5月上旬,我站在托克逊县夏乡色日克吉勒尕村的大片孜然地里。这片孜然地有数百亩,是成片单播。但更多的孜然套播在棉花地和玉米地里。此时的孜然,一半在开花,一半开始结果。细小的紫色花朵缀满枝头,随风摇曳,闪现在一望无际的绿色中。村民们在为孜然锄草,近旁的麦子在静静抽穗。
记得在乌鲁木齐时,孜然专家张谦告诉我孜然开花的特点是“无限花序”。也就是说,每一株孜然都在尽最大的努力,使自己的复伞形花序无限繁衍、开放。这几乎是对自我极限的一次挑战。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,孜然开花就像节日的焰火在夜空无限盛开。所不同的是,礼花过后是空洞的夜晚,孜然花开过则是芬芳的、丰收的原野。
我蹲下身子,仔细而入迷地观察一株正在开花的孜然。英国诗人丁尼生说,当你从头到根弄懂了一朵小花,你就懂得了上帝和人。面对一株孜然,我也想说同样的话。
孜然的学名为枯茗(CuminumcyminumL.),也叫安息茴香、野茴香,为伞形花科孜然芹一年生草本植物。它的原始产地在北非和地中海沿岸地区。
目前世界范围内种植孜然主要是印度、伊朗、土耳其、埃及、中国和前苏联的中亚地区,基本上分布在从北非到中西亚的干旱少雨地区。由于孜然是制作咖喱粉的重要原料,印度是世界第一孜然大国,它的西部地区普遍种植大粒子孜然,品种也与别的国家有所不同。
新疆孜然为伊朗型,品质介乎印度型和土耳其型之间。它是通过丝绸之路从波斯传入古代西域的,与胡椒、没药、安息香的东传有着大致相同的线路。
新疆曾经是我国孜然的唯一产区。主要分布在东疆的吐鲁番、托克逊县及巴州的焉耆回族自治县,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县、沙雅县,喀什地区的岳普湖县、疏附县,和田地区的墨玉县、皮山县等,北疆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也有少量栽培。2005年种植面积达70万亩。近几年从新疆引进后,内蒙古、甘肃和云南也有了一定数量的种植,但新疆的种植面积仍占到全国的80%以上。
孜然不仅是新疆最重要的食物调料,也是维吾尔药中必不可少的药材。药理表明,孜然果实及挥发油有驱风、兴奋神经、健胃、抑菌作用。主治胃寒呃逆、食欲不振、腹泻腹胀、小便不利、血凝经闭等。孜然飘香的街区
在乌鲁木齐市二道桥、喀什老城、和田大巴扎等一些孜然飘香的街区,孜然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一座城市的门。借助孜然的香味和感官的陶醉,我们似乎能一下子抓住城市的灵魂。因此,我称这些地方为“孜然街区”。它们常常是城市最古老的部分,是热闹的商业饮食区,同时也是最具魅力、最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。
不少旅行者是通过气味来发现并喜欢上乌鲁木齐的。这就是这座城市大街小巷到处弥漫的烤羊肉串、各色馕饼、热腾腾抓饭的香味,尤其是孜然这种 “首席”香料的气味。它先是抓住你的嗅觉,继而征服你的胃口。就像普鲁斯特笔下的小玛德莱娜点心,多年之后当你在别的地方闻到类似的气味时,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在新疆旅行时度过的难忘时光。
作为乌鲁木齐最著名的维吾尔族聚居区,二道桥是中亚美食博览中心,是一席流动着色彩、音响、气味的盛宴。当然,我更喜欢那个 “沿街为市”的老二道桥,街上人头攒动,烤肉炉烟雾缭绕,建筑(尤其是几座木结构的清真寺)有时光的沧桑感,给人一种踏踏实实、真真切切的“在人间”的感觉。而改造过的二道桥,尽管洋气了,现代化了,却多了些刻意的、香艳的色彩,少了些原初的朴素和世俗化的亲切。假如有一天,烤肉炉和馕坑纷纷向室内转移了,古老的街区将变得面目全非,留下的只有叹息了。
在二道桥,孜然独特的芳香来自烤肉炉、馕坑,来自快餐店、宴会厅,来自调料铺、药材店……孜然无处不在,它的芳香四处飘游、弥漫。是孜然激发了维吾尔饮食的特点:质朴、浓郁、热烈。这种特点与新疆大地呈现的气质和风格是一致的。一个地方散发的气味也会打上这片地域的印记。
我不知道孜然这种波斯香料是什么时候传入西域的,但回顾人类的历史,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,对异域香料的需求和热爱由来已久。马可·波罗在描述13世纪的杭州时说,这座城市一天就运来了5吨波斯胡椒。他还说:在中国南方,有钱人可以享用好几种香料腌制而成的肉,下层民众的盘子里却只能嗅到大蒜味。
“香料滋润人们的生活,使生活变得更为丰富多彩:它是药品,可以治病;是调料,使饭菜更加可口;是香水、润肤剂和春药,可使人心旷神怡。” (马斯格雷夫: 《改变世界的植物》)
爱德华·谢弗在 《唐代的外来文明》一书中指出,几乎所有的香料都经历了一个从神坛走向世俗的过程。古时候人们常常在祭祀用的酒和肉中加入香料作为调味品,目的是为了防止祭品腐坏,增加祭品对于神的吸引力。后来,香料渐渐世俗化了,走下了神坛,搬上了贵族的餐桌,甚至还进入了寻常百姓人家。
我不知道孜然是否也经历了从神坛到世俗的演变。但细究孜然的风格特点,它的身世与沉香、没药显然是不一样的。它绝对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那种。它的芳香浓郁而热烈,紧贴着大地。其天生就属于民间,属于大众,属于世俗生活的光阴和食谱。
二道桥,孜然焚香的街区。一个二道桥的烤肉炉就是一个世俗的、肉感的、烟雾袅袅的 “焚香炉”。 “一串肉在火上尖叫/就是一只羔羊在火上尖叫,是一百只羔羊在火上尖叫/多少只羔羊已葬身人的口腹之坟!” (《混血的城》)
维吾尔族人称烤肉为 “喀瓦普”,是对烤羊肉串、烤全羊、馕坑烤肉的统称。当然还应该包括南疆更为原始的烤肉:立体烤肉 (架子烤肉)和火埋羊肚子烤肉。在新疆城市街头,烤肉是最为普及的风味快餐。一个烤肉炉,一点细盐、孜然、辣椒面,就能烤出美味可口的羊肉。滋滋冒油的肉串,孜然的香味,还有烤肉师傅的吆喝声,成为一幕幕生动的街景。三五朋友,围桌一个烤肉炉,喝着地产的啤酒,海阔天空地聊着,不亦乐乎?不亦快哉?
值得一提的是,南疆和田等地的一些烤肉师傅从来不用辣椒面,只用孜然和盐。因为在他们看来,辣椒面既改变了烤肉的风味,又能掩盖羊肉的不新鲜。为了烤肉的纯粹,他们只信任孜然和盐。
一个烤肉炉不仅用来烤羊肉串,还能用来烤羊排,烤羊杂、烤羊肉丸子、烤牛肉、烤鸡肉、烤鱼、烤玉米、烤蔬菜,等等。一个普普通通的新疆烤肉炉,轻而易举就能烤出一席街头盛宴。
烤,古称炙,作为烹饪法的一种,有着悠久的历史。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2200多年前的有关饮食的遗策中,就有 “牛炙”、
热门招聘
相关主题
- 梳理中国历史上十大国耻级事...
 [5426]
[5426] - 出差在外求方便工控人地图
 [13243]
[13243] - VACXN惊爆删贴门!真相无隐,事...
 [6835]
[6835] - 中年人,这里有多少,可以一叙...
 [9668]
[9668] - 台达B2伺服在什么情况下会报...
 [7876]
[7876] - 我熟悉的那些工控论坛的男人...
 [9702]
[9702] - 工控刀吧:喜欢玩刀的兄弟请进...
 [28869]
[28869] - 系统学习自动控制应看那些书
 [6598]
[6598] - 神奇的图片——同构图片!
 [8753]
[8753] - 出差攻略--越南河内出差攻略...
 [4980]
[4980]

官方公众号

智造工程师
-

 客服
客服

-

 小程序
小程序

-

 公众号
公众号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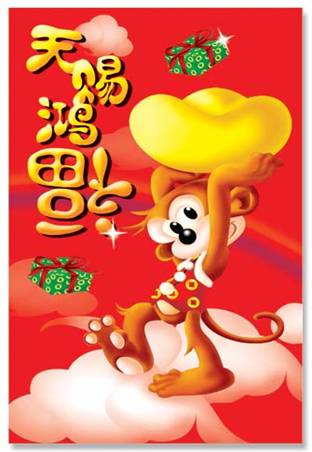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 工控网智造工程师好文精选
工控网智造工程师好文精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