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动化正在成为一个吃软饭的行业 点击:163 | 回复:0
今天,很多企业开始宣称“软件定义自动化”、“软件定义制造业”。其实,早在2013年,美国著名的媒体连线(Wired)就以更为宏大的叙事制造了“Software Define X”这个词。当然更早的是斯坦福大学在2006年就提出了“Software Define Network-软件定义网络”,然后“软件定义汽车”等各种概念就出来了,今天人们开始高呼“软件定义制造”、“软件定义自动化”。软件定义是有意义的—因为,它的核心要旨在于用软件来应对变化的世界。
记得去年传动网苏姐采访肖博,当时肖博说了句“自动化以后是个吃软饭的行业”—觉得这是个好话题,一直试图去描述这个话题。今天,大家说软件定义制造、软件定义自动化,其实,通俗地说,就是我们自动化行业越来越多靠软件赢得未来的生存。
实际上,自动化早已是一个由RTOS、行业工艺软件、网络连接、HMI、AI、标准化如PLCopen构成的软件系统。而图1则是在十多年前就绘制的一个关于“软件价值”体系的描述。

图1-自动化的软件价值体系
那个时候,我们绘制这个的核心叙事在于“软件构成了核心竞争力”—但这个叙事是给用户来说明,他们的机器中差异化竞争力来自软件,这里核心在“工艺”。也就是之前我和“工业软件”群经常谈到的一个话题,即,除了看得到那些以产品形式存在的工业软件,还有大量尚未受到足够重视的。即,隐藏在嵌入式系统里,每台机器里的软件,以及生成这些软件的软件。自动化行业里,平台工具软件如Automation Studio、Portal、Logix、EcoStructure、TwinCAT等。
之所以软件定义,是因为VUCA这个词所描述的世界正在悄然发生,且更加加剧—以消费世界为例,它的各个维度的改变正在给制造业带来极大的难题—在理想状态下,企业自然希望通过极致的规模化来摊销成本,进而获得极致的成本优势。如图2,VUCA带来了复杂性,需要得到有效的解决,数字化被赋予了重任,这个也就以各种软件的形式来实现。

图2-VUCA时代数字化的意义
在一个产品需求更为复杂的时代,让制造企业,尤其是那些代工企业,他们会必须面对众多的产品需求,这些需求还特别的碎片化。并且,还需求特别的着急,因为人们习惯了明天就能收到货,如果是后天就可能放弃购买。
软件定义制造的不断演进
1.运动控制实现产品变化的生产
所以,一种灵活的、可重配置的产线是迫切的需求—这个通过传统的机械调整,就会非常的慢,且成本高昂。因此,制造业的自动化一直在寻找更为妥善的解决问题的办法。这样,就产生了灵活的机器来改变配置,机器的控制+伺服控制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。在30年前,在机器里采用伺服电机,是为了实现更高的加工精度和速度,但在很多机器上,伺服电机并不在同步时工作,而是在机器换单的时候,对机器进行调整。例如,裁切刀的刀辊换成伺服驱动,这样,裁切尺寸变化的时候仅需参数设置即可执行新的裁切任务—当然,这里的伺服电机本身是作为一个同步轴的,它会跟随被裁切纸张的尺寸。但是,在印刷机的斜拉版、压印力调节、机械的机构调节,在瓦楞纸的换刀、书刊胶装/骑马订等场景里,伺服电机仅在需要更换规格时动作。然后不参与同步的电子齿轮、电子凸轮等动作—这里大量伺服电机的使用就是为了灵活的应对产品规格的变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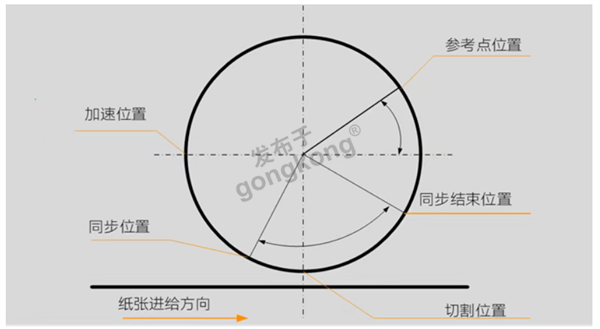
同时,为了实现这些机械加工的效率,又实现了连线生产,像饮料的吹灌旋贴,开清棉、长流程的离散制造都在实现这样的连线,中间更多使用机器人、AGV是为了提高效率。因为,必须把换单造成的那些时间损失都得弥补过来—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网络来把整个机器连接起来,而不是用硬接线的方式来实现启动同步。通信就成为了实时控制的关键一环,而这些机器可以通过这种统一的通信连接实现同步,在软件层,对这些参数的上下行进行读写就成为了机器配置的关键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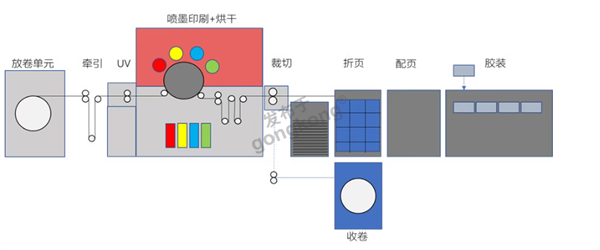
图3-连线生产,从印刷到书刊输出
运动控制的问题是它主要在机器内,例如定位主要解决单点的问题,同步也仅解决多个轴的关系,但它无法解决在机器和机器之间的输送这个难题。
磁悬浮输送解决机器-机器间的可定义性
进一步的,人们发现控制主机实现了软件定义的任务编排,网络实现了数据流动和交互的接口,但机械的输送还是个难题—当年,CIMS/FMS这些其实就因为这个原因,无法被有效的运行。因此,才产生了柔性输送系统,即,现在被称为磁悬浮输送的系统,它打通了最后一个难以被“软件定义”的环节。通过“电-磁”转换,将传输系统转为可以被软件定义的“单件流”、“连续流”—这符合精益对于产线的编排需求,因为它可以实现排队、配合加工等,可以让物料流动、配合加工成为一个被软件快速可重配置的形式。这进一步推进了软件定义制造的可能,如图3所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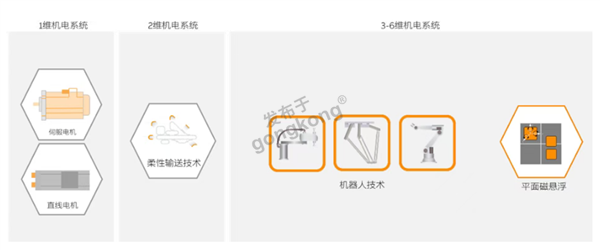
图4-运动控制从一维增加到六维
因此,伺服电机、机器人、磁悬浮输送解决了产线中的局部修改,以及在机器间物料流的解决。
通信-解决协作中的信息流
在软件层面,人们实现了加工过程的状态建模来实现生产的重组—用软件的“编排”来实现生产线的重组。之所以,采用状态模型,就是因为它可以被逻辑编程。像PackML、JDF、ISA-95、IEC61850、Unimat等垂直行业的规范,就是为了能够对这些生产过程进行统一的行规设计—这样就可以快速的参数下发。而新的MTP则是针对自动化系统的统一规范,来实现工厂的管理层任务解析并下发—可以通过OPC UA来实现这些通信的连接与数据的封装,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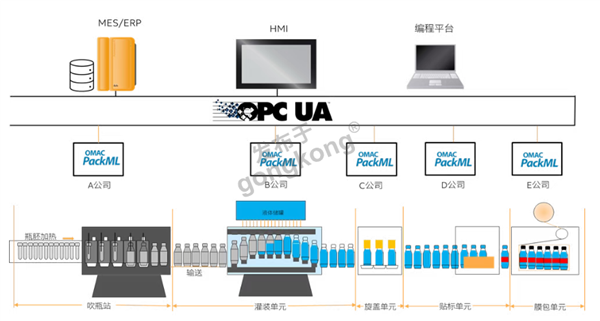
图5-PackML协作横向与纵向的机器联网
物理建模与AI-解决知识的复用问题
对于制造业,如果每次都要对一个任务进行编程,或者对于一些知识都要重新组织,那么工作量还是很大的。为了把知识进行有效的复用,工程师们就开始想在知识封装上下点功夫。
在知识的挖掘的几个典型范式里,人们经常把远古时代的科学发现定义为人的天赋来实现的。而基于笛卡尔的方法论以及牛顿、莱布尼兹这些伟大科学家在第二个阶段,人们开始将物理的公式作为解决问题的思路。而在计算机出现后,这些物理模型的验算就成为了计算机要去干的事。但是,这种基于物理知识的毕竟是有限的,它需要先验知识和已有的数据积累,才能更为精准的模型。而这无法满足越来越复杂的世界对于知识的苛求。那么,新的范式,基于AI就成为了一个必然的选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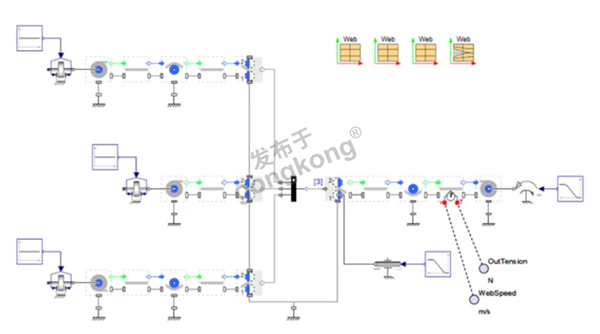
图6-MapleSim的张力控制建模与仿真
再进一步,人们又发现这些系统由于过于复杂,且存在很多“不可见的深渊”—即,在复杂的系统里,他们会产生效率无法被最优的问题。因为,复杂系统,它的路径规划会形成非常多的组合,这无法被人用公式来计算—因为,这是一个“陷阱”,就是被窝在系统里的能力,它无法被有效的发掘。包括引发生产产品品质的干扰因素,例如相关性的、随机误差造成的无法被有效的观测和梳理。这就使得人们寻求通过“数据驱动的建模”来挖掘这些背后的规律。产生了对人工智能的需求—而人工智能,则又是一个软件。
软件的模块化-实现知识复用
用高级语言封装算法,且构建出“高内聚、低耦合”的应用模块,然后让这些模块快速重组,来搭建整个机器的应用程序。这个就是要用模块化的软件开发来实现—但是,自动化它所面对的机电又是一个高耦合的领域,因此,基于物理建模的方法在计算机出现后就开始被大量使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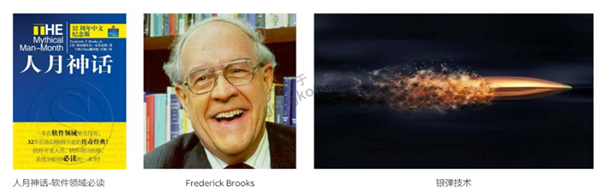
图7-软件工程的模块化思想
在软件工程领域,著名的工程师Fredric在70年代,觉得软件正在陷入泥潭—后来随着模块化技术的普及,软件的危机在被解决。在制造业同样如此,人们通过模块化来实现机器的快速软件重组。
AIGC编程-让工程迈入更为灵活的时代
随着系统的复杂性不断提高,我们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算法、AI分析、界面等,程序会变得越来越复杂。传统的编程即使是增强模块化,仍然不够,因为它的门槛也比较高,尤其是机电工程领域。
AIGC编程就成为了一个潜在的方法,因为,它会继续使用原有的知识、模块来为工程师快速搭建架构,进行“按需”软件设计。尽管它目前尚不是很完善,这里,尤其是指制造领域的机器和产下,但,如果能够定义统一的规范进行约束,那么,相信它的准度、深度进一步发展。其可用性会更高。
据此发展下去,软件未来自动生成软件,自动化工程师则将成为一个顾问,或者一个“桥梁”,它连接用户端模糊、不确切的需求,以及组织复杂的机电工艺之间的“关联”与“架构”。即,未来需要的是机电、工艺系统的“架构师”,而不是“Coder”。
基于建模的开发与模型交互
但是,这个还不够,毕竟,在机电领域里,不如纯软件领域那么方便。太过于碎片化,因此,采用物理仿真的自动代码生成也成为了一种办法-Mathworks就在2008年推出了为自动化领域的工程师们开发的SimulinkPLC,通过C代码的生成来实现模块的生成。Modelica组织则试图在不同的机械软件间进行模型的数据互换,开发了FMU/FMI接口,这个不仅在纯的CAD/CAE软件之间,也在物理建模和自动化软件间进行了这样的接口。当然,后续OPC UA会接续这个模型,使得其更为广泛的连接到不仅基于模型工程(MBE)的领域,如云端系统、垂直领域的软件之间的接口数据统一。
因此,我们可以看到,要实现“软件定义制造”。想吃上软饭,这个链条里的基础操作系统、硬件的嵌入式软件、实时网络到多业务流数据的汇集、行业规范、数字化设计软件、开发工具、AI、云端,这一切都需要进行有效的组织,形成有机整体,这个事情才能真正被实现。
软件定义制造的未来的难题?
软件定义制造,就目前看,还有很多现实的难题需要突破。真正想吃上软饭,还是需要解决一些关键的问题,并非仅仅技术的。

谁为这些软件买单?
软件必须成为一种有效的盈利模式,硬件可以统一设计制造,由OEM/ODM厂商来代工生产。而每个企业的竞争力将由是否能够解决特定问题,实现以软件、服务为主的盈利。
要真正实现“软件定义制造”,就必须确定软件的价值,并将软件成为一种严格封装的,知识产权边界明晰的产品。且,能够独立的运行在跨平台的系统上。
要实现真正的软件定义制造,有几个方面必须做到:
1).软件的独立性,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在IT业界采用了包括容器技术、Docker等各种方案,这些方案对于IT系统架构在统一的硬件上而言,相对比较容易。因为,纯软件行业,他们的规范性是足够的—而在制造业,这个软件的标准实现就由于过于强耦合的硬件、操作系统,而难以真正做到隔离。
因此,未来的自动化系统,它应该是操作系统更为通用,例如采用Linux,RT-Linux,且实现与开发环境的剥离。应用软件可以脱离厂商的硬件,在通用的硬件上来实现部署,例如你可以把它部署在嵌入式系统,也可以在PC、服务器、云端。
2).软件必须是可以被独立销售的
这个环境似乎目前还不能看到,只是有些端倪,毕竟,长期依靠硬件吃饭的行业,真的把软件剥离出来,会伤害既得利益者的盈利能力。这是IT业界进入制造业一直试图去颠覆的,尽管这个步伐看上去很难。这也是制造业的特殊环境—因为,可靠性、稳定性的需求是基础需求。
但是,这并非不可完全解决,即,纯粹的硬件厂商+IT的能力,因此,这个时候,自动化和这些试图进入制造现场进行颠覆的人就产生了冲突。那么,这就会看谁更能坚决的带来商业价值。但,作为自动化领域的厂商必须去开放的接受这个事实,依靠硬件或软硬结合的方式肯定是个能吃5-10年的,至于再过10年后,会发展成什么样,就不好说了。
3).统一标准与规范的建立
为了实现各个层级的软件的南北向数据、东西向数据的打通,统一规范是必须的。这个规范究竟是什么?是OPC UA吗?目前这是个选择,但也未必就是唯一的选择,当然,OPC UA可以把各种选择都给纳入它的框架之下。因为,它与IT那些标准规范具有先天的工程思维。
可能制造业会不同,相对比较严格的—现在的很多标准尚未被有效的使用,就是因为在实际的“智能连接”上需求尚未真正达到一致。因此,很多概念仅在前沿的企业那里会看到雏形,或者试验型产线。
在各个软件间形成快速的接口数据交互、以及程序间的交互—就像MTP,如果自动化厂商都遵循MTP,那么,当产线上的数据进行了修改,它也可以被下发给不同的PLC,并且,写入变量中,或自动读取。如果AIGC编程也能按照这个接口标准来定义对象、数据格式,那么是否意味着,即使是它生成的程序,也可以被PLC直接读取呢?这个约束机制,本身就是一个探索过程,但,用“规则”约束自动编程系统。在可行性上可以进行探索—软件自动构造的方法,既可以通过系统建模、语言建模、软件接口、模型接口—至于那种方法更好,可能通过多个接口和机制的联合行动,大家也是可以做到最终的交互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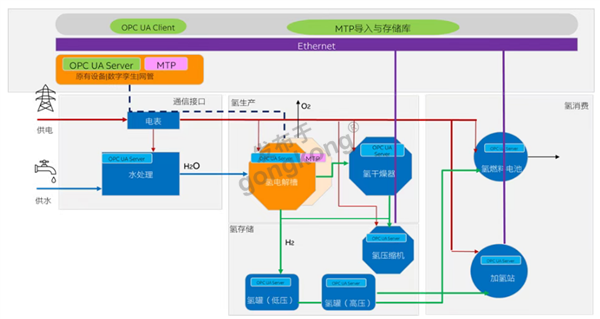
图8-MTP用于在氢电解槽系统里协作
在图这个架构里,电解槽相关的水处理、变流器、压缩机、电解槽、干燥系统、存储系统之间会形成一个整体。当系统需要更新数据和升级配方,则会统一的数据下发,以实现远程的升级。
这些工具的最佳组合—会被探索出来,例如,在通信接口方面,模型交互方面,其实,不必完全构造,而是让系统学会各个接口规范,并让程序按照这个接口来实现—反倒,这个可能对于推理强的AI更容易掌控局面。因为,我们要做的太复杂的时候,人反倒是难以实现的—但,人可以为机器提供校验,它还会学会你的校验过程。
4).自动化还得是个咨询公司
前面提到,如果我们希望做到软件定义制造,而又有AIGC编程、模型交互、模块化设计,凡此种种。我们也说了,这个能够让机器和系统更快的自动构造。而这个时候,你会发现,最为重要的不再是编程,设计,而是“架构”,即,用户的需求到实现之间的这个桥梁。
将用户需求翻译为机器可实现,这并非易事。因为,人的需求往往是模糊,不确定的,且存在隐藏的、没有被发现的—甚至提出需求的人自己也不清楚。
那么,这个时候,其实特别需要具有“咨询顾问”能力的工程师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即,它能够梳理需求的逻辑,并能对需求进行精确的定位,并且,能够关联机械设计、电气、工艺、AI分析之间的关系,它能够把它表达为Prompt去给AI系统。让它去实现,然后还能给它的实现进行修正。
这可能不是一个工程师能完成的,而是一个由多个人和跨企业专家构成的团队,但这个团队需要具有咨询顾问的提问、分析能力—它不止于跨学科,还跨职能去实现项目的组织。
5).知识产权保护
要想真正实现软件定义制造,那么,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,就必须有非常强的机制。当然,这种机制不一定是法律的机制,也可以是技术的实现方法,配合法律法规。
这里也会牵扯到非常多的权利问题,即,数据权属问题、知识的归属,以及复制的权限。包括信息安全保护机制确保数据资产的安全。
所以,这个吃软饭,能成为一种稳定的饭票,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发展。从目前来看,这个方向有端倪,但尚未到真正意义“软件定义制造”。
来源:微信号 说东道西
楼主最近还看过

官方公众号

智造工程师
-

 客服
客服

-

 小程序
小程序

-

 公众号
公众号

















 工控网智造工程师好文精选
工控网智造工程师好文精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