隐藏在通信背后-如何应对复杂制造系统的软件协作 点击:289 | 回复:0
1.通信在制造系统的水平集成
在一个End User的工厂,它会出现不仅是某个设备的集成,例如一个电子工厂,它可能会牵扯到注塑机、CNC、贴片、包装,各种设备,那么,他们如何被统一协作?
VDMA试图构建一个适用于各种机器的状态模型,以及基础的信息模型来进行“一统江湖”,虽然感觉有点难,但这种精神值得赞扬。最新的OPC基金会的在线会议内容里浏览了一遍,看到VDMA试图要去构造如图1场景中的连接问题,即,在一个包含了切割、涂装、包装及检测的流水线里,这些机器间如何通过状态来实现协作。它定义了不多的状态机-执行(Executing)、不执行(Not Executing)、停止服务(Out of service),不可用(NotAvaliable)四个状态。不过,我的确觉得这四个状态如果对于复杂机器来说,也许计算可用性是够了,但如果计算OEE的话,就得看其他的参数是否足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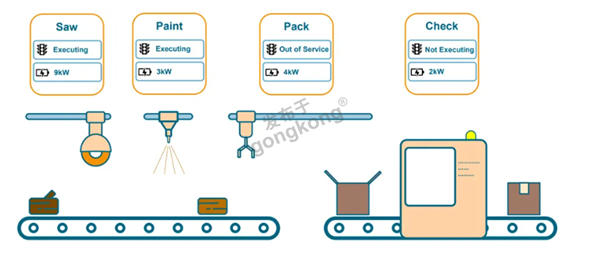
图1-VDMA的机器状态模型
但是,如果其伴随信息模型-就目前的信息模型来看,仅包括机器ID、监控(状态、运行模式、健康状态、消耗)、机器设备、通知、作业单信息。感觉还差点意思,想要达到如图2的计算,如OEE、DPP的计算和访问,实现数字孪生的交互信息、AI应用的数据交互,现在这个CS(所谓的伴随行规)还是不够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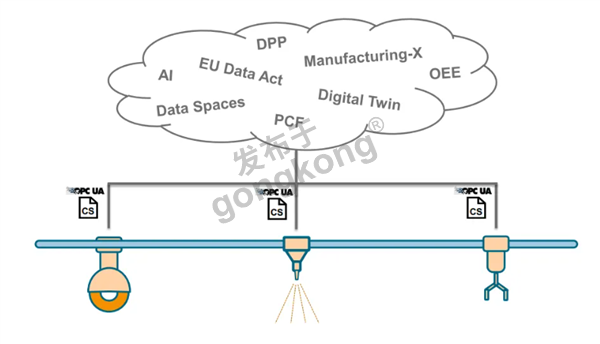
图2-计算产线相关的数据与实现应用
对于这个伟大的想法,之所以觉得难,因为现实中,似乎只有SEMI的行规用的最好,但它并未基于OPC UA来实现。SEMI的规约整体就像G代码,它给每个命令行定义了对应的操作,以及携带的参数,机器的任务就在一个简单的G代码下就可以运行。SEMI其实是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,就是在半导体的生产链上,所有的设备操作的对象是单一的,即那个被称为“Wafer”的东西,不管你是个退火炉,还是个光刻机、沉积、刻蚀、离子注入、抛光设备,但你们的加工对象其实是一致的,你们每个设备所进行的操作如上下料、工艺过程、检测,其实这些动作对应的参数(起始位置、路径、时间、温度、压力这些参数)都是围绕这个晶圆本身的。同样,就像TSN在汽车行业容易被统一,因为汽车都是四个轮子+悬挂+发动机(电机+逆变器)--从物理对象建模的视角,这个对象也是单一的模型。
通信的行规,其实就定义了在自动化的编写任务时,以更为结构和逻辑形式去操作这些机器之间的协作。因为所有的机器都是“动作”+“参数”、按照逻辑来运行的—就相当于每个子程序调用,在新状态下调用新的子程序(携带参数),而这些行规就定义了这些动作及所带的参数格式。所以,通信行规它简化了整个自动化程序的编写。
2.垂直行业的快速信息采集-垂直行业信息模型
在不同行业,我们如何去快速地搭建运行系统,让机器之间形成协作?虽然,这种行业的信息模型非常难以被适用,就像前面提到半导体SEMI人家对象单一,你包装的PackML,也推了有30年了吧,但是,你看究竟End User那里谁用这个了?因为,你包装领域这个机器实在对象太复杂了,像液体、固体、粉体他们就包装形式不同,你就制药包装里还有片剂、丸剂、胶囊制剂、液体制剂、气雾剂,这种复杂的对象变化,让人家很难统一啊!
当然,这里想说的不是这个难,这个难主要是大家还没有到高度的“工程集成”阶段,各个行业现实中,也未能实现真正的所谓“智能制造”,因为,连线才能显示这个制造的智能啊!只有连线的生产才能需要更为“实时”的协作,而单机仅在其动作间的工艺切换—产线则是全局的协作。
问题不在这里,而在于“软件化”的问题,即,标准的软件化设计。这很关键—即,我们如何看待标准的问题,是否我们制定的标准能够被软件化形式被自动化系统快速“配置”,标准不是一个文人骚客写的文档,而是基于工程需求来设计的一个产品,一个可复用的知识和“规则”。
PackML在这方面堪称典范,它完美的制定了机器和系统如何被状态机协作,以及从最小的组件到整个产线的模块化设计。在作业管理解析下发到每个控制任务的参数中,以实现生产的变更。
PackML是个很好的通信行规设计范例,它解决了几个问题:
1).进行资产管理,计算OEE时,根据每个状态的计时来计算可用性(Avalibility),根据良品率(Quality)统计、机器的实际运行效率(Performance),这三个指标就可以计算OEE。
2).它定义了很好的单一操作界面,机器无论如何复杂,其在多个状态间切换,实现了逻辑的任务编程与组织。这也是一个对用户友好的方式,用简单的逻辑来编排任务。
3).机器的信息模型提供了整个数据采集的效率,通过打包的数据来实现快速的工程数据采集。
从自动化工程的视角,通信的行规其实定义了一种快速的任务调度机制,即,当作业变化时,快速的用状态逻辑来配置生产成为可能。因此,通信行规,它要解决在整个变化的生产中,如何快速的进行Engineering的参数配置,而不是复杂的编程。
3.云端系统与数据源的连接-从传感器到云端的连接
越来越多的工厂,需要从底层到云端的数据,以及部署在云端或边缘侧的控制与调度优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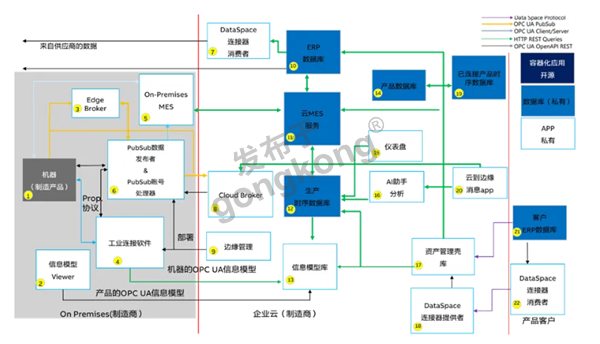
图3-云倡议中的通用架构
在图3,OPC基金会的这个云应用的倡议架构中,其实,它提供了机器与产线端的数据,通过OPC UA Pub/Sub、C/S机制、OpenAPI Rest、REST Queries的方式来形成各种数据交互的支持。这个架构包括了微软、华为、亚马逊作为主要的推动者。
在图3的复杂架构中,采用了非常多的数据分发机制,来为显示、产品管理(消费者相关)、MES(云端MES)、ERP(云端ERP)、AI分析助手等,提供了各自的数据分发机制和协议。这种纯软件的领域,他们可真是不嫌烦,还定义了很多—当然他们比较熟悉,也会快速简单配置即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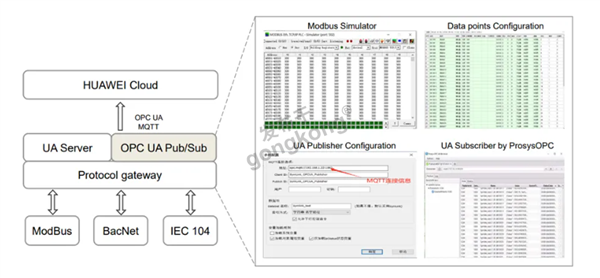
图4-WebAPI的连接方式
图4是我在OPC基金会的报告里看到的来自国内的自动化企业,D同学是老朋友,在OPC基金会的报告是关于WebAPI的方式,直接在浏览器端采用Web Client/Web Service的方式来提供对OT端数据的直接访问。这是个好办法,其实,现在的PLC有个Web Server也很正常,通过浏览器来作为访问,自适应性、易于开发的特性还是挺好的。也算是对OPC基金会发挥了中国的贡献。这很关键,支持WebAPI的OpenAtom组织也的确是由中国本地的华为、阿里、腾讯发起的。我觉得这是个很好事情,本土企业在全球的标准组织了起到这种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4.工业控制与CAE软件的协同-OPC UA的模型交互
为了构建数字孪生,需要在动态的方式连接这些软件之间的关系。最早时候,这个仿真类软件与自动化类软件的接口都是“私有”的,就像Mathworks针对不同的自动化公司,都开发个Connector的接口。后来,Modelica组织就开发了个FMU/FMI在各个CAD/CAE软件间来实现交互,包括自动化公司也支持这个,像SIEMENS、Rockwell AB、B&R、Beckhoff这些都有这个接口。这就相当于私有到专业,即,这个专业组织内部大家可以交互。不过,可能未来还是OPC UA能够跨领域,因为CAD/CAE/EDA之间还是个专业系统,OPC UA要打破这些专业之间的协作,还要跟MES/ERP、云端、AI系统进行交互,需要更为通用的接口。
这个接口对于自动化的好处其实在于“自动代码生成”,像Mathworks的自动代码生成可以为核心算法封装和下载到本地PLC,进而实现硬件在环测试,加速开发效率和降低自动化系统的开发成本。
这些接口与规范,正代表了协作范围的不断延伸,产业的不同领域必须打破那些横亘在所谓专业领域的“藩篱”,打开这些影响协作与全局优化的阻碍。这也是整个数字化要进行的工作前提,任何所谓的数字孪生、人工智能的分析与优化,都必须建立在这些藩篱打破的全开放世界。
开放将突破专业领域,也将突破层次结构,即,在横向与纵向打破壁垒。
5.管理相关信息模型DPP/碳追踪
之前看过关于DPP在绿色包装产品方面的,但现在看来,这个DPP可能更像是个针对动力电池、消费电池这个领域的一个壁垒。不过,欧盟这个DPP的参与方,感觉还得是国内的电池厂商比较多,CATL、BYD、亿纬锂能、阳光电源这些厂商,毕竟,欧洲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拿得出手的电池制造商。它这个标准,还是得与全球主要的电池厂商,那90%都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。除了这些问题,包括像DPP-数字产品护照、碳足迹这些贸易相关的内容,也需要从机器来采集数据(Embedded DPP),以及为了实现碳追踪,在机器的系统里对能源相关数据进行采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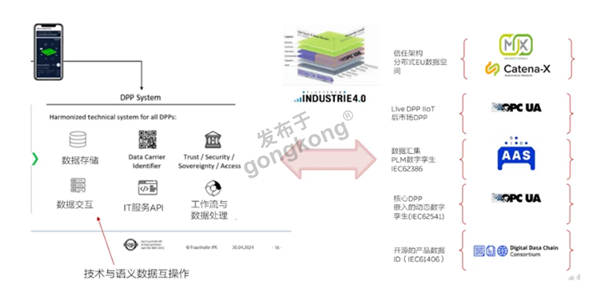
图5-数字产品护照DPP运行与数据实现
所以,OPC基金会和ZVEI、CATENA-X这些组织一起来实现这个DPP的嵌入式数据采集方案,包括在BMS里的数据点,以及在销售流通环节、处理后环节的各个数据的监测。其实,也包括了碳足迹的追踪问题—在去年的报告里,OPC UA也定义了碳足迹和碳捕捉的数据采集,这个可能会和绿色电力的贸易壁垒还是有关系的。就是要知道你制造这个产品的电力来自哪里。
6.统一工程规范MTP
对于自动化系统而言,如何在分布式的系统里,实现数据间的工程,这就像,系统里由5个不同厂商的PLC厂商来实现的各个单元控制,现在系统的任务变了,如何让每个单元都能去升级他们的系统,怎么样才能把变更,通过一个接口写入到每个控制器的逻辑或算法单元?
Automation ML试图构建这样的方案,但似乎也并未能够很好的实现,现实是Automation ML并未被大多数的公司作为一个模块嵌入在系统中。
不过,MTP则似乎正在成为一个热点,它试图去为分布式系统定义一个工程的统一接口,以便能够为这种分布在多个地点的,由不同的组件构成的整体系统的升级带来工程效率的提升。
因此,对于自动化系统来说,工程集成—通过这种统一的规范就可以很快的实现自动化任务的集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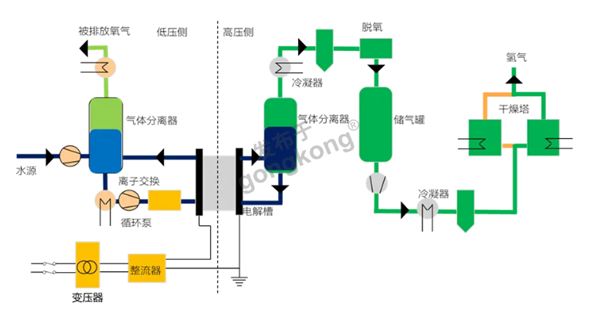
图6-氢电解槽的构成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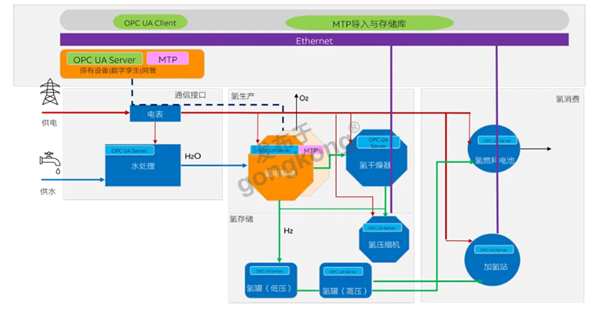
图7-MTP在氢能系统里的架构
图6是去年还研究了一下Power to X(消纳清洁能源,转为绿氢,再转为X-甲烷、绿氨、汽油、甲醇等,统称为Power to X,即,电转各种能源X)其中核心的电解槽结构,以及通过MTP为这个制氢系统搭建的工程服务架构。
不过,最近听说欧美的很多大型的氢能项目都停止了。这个其实清华大学一位专家在大约8年前就做过分析,电价如果均量化度电成本(LCOE)不能低于0.25人民币,制氢这个路就不具有经济性。因为只有中国的光伏和风能的电价可能才能干到这个数左右。另外,从清洁能源消纳角度,可能中国才有Power to X这个必要性。
当然,这部分就算闲扯了—本来我这个文章想说的其实是,通信规约对于自动化工程的角色,以及其核心作用。
越来越复杂的集成,以及IIoT和AI应用,这些使得工程集成变得复杂,那么快速的搭建这种信息模型、数据交互接口规范与标准,还是很有必要的,OPC UA提供了一个好的方向,不过,戴老师总是说OPC UA太重了,的确是—他们也雄心勃勃要干出一统江湖的通信。什么都往里面加,今年的OPC基金会的报告浏览一遍,包括信息安全、针对垂直行业的(激光系统、铁路系统、航空系统)、能源问题的,机器的统一通信行规,还把各种通信都要纳入,TSN/WiFi/5G,啥都想干。
私下里和戴老师等也讨论过这个问题,为什么像IEEE/IEC这些组织能够把这么多来自不同领域,很多竞争的企业抓到一起来为未来的发展制定标准,这个也是个挺厉害的事,这种组织运行机制也挺有意思。
来源:微信号 说东道西
楼主最近还看过

官方公众号

智造工程师
-

 客服
客服

-

 小程序
小程序

-

 公众号
公众号

















 工控网智造工程师好文精选
工控网智造工程师好文精选
